我应该算很喜欢光影,像泼洒彩漆---喷薄而出的跃动和凝于白纸的优雅。吱呦转动的胶片,从容叙事;缓缓沉落的胶底,浅唱低吟。然而,我恐怕只是个“光影他人”的叶公,或者是惧怕“摄魂”的灵异,我似乎从来没有面对镜头的天分和坦然,常常手足无措皮笑肉不笑肌理僵硬反应迟钝的展现着,我是如何在面对镜头的那一刻智商骤降为零。
关于拍照这回事,对着手机大头贴立可拍数码机瞪大双眼尖起下巴的兄弟姐妹们,是想用某一刻的美好说服自己还是他人呢?我应该是害怕定形的影像说服了自己,眼前这个目光呆滞神态猥琐的脸孔,暴露了我全部的恐慌和忐忑,我不再安全,起码不如以前那么安全,似乎授人以柄,梳着满头小辫到处招摇。
所以,摄影大师们瞬间表情的拿捏是绝妙的,可是,表情一定不能是自己的。这大概和医者“能医人而不能自医”差不多。拿着刀子,一边解剖自己一边做实验笔记,这是好莱坞三流血腥惊悚变态恐怖导演们杜撰的情节。
不过是照个相,可是没什么安全感的神经质比如我,就是可以搞得这么矫情麻烦。
不是还有人说:“影像,传达信息,提供快乐悲伤,影响风格,决定消费,并且调节权力关系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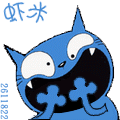
简直捧成All Mighty了嘛!轮得到我和你聒噪吗?
貌似,本雅明介绍某个超现实主义摄影师时,称赞其作品回归现实,划破了以城市之名挑起的异国情调浪漫及看似冷漠的共鸣,他说:
“这些照片从现实中汲取的灵氛就如同把水盛出半沉的船一样。”
按照老本的解释,灵氛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奇异交织,静歇的夏日正午,目光追随远去地平线上的矮树,他们将观者笼罩在自身投下的荫影里,后者已然成为风景的一部分-----这便能呼吸那远山树枝上的灵氛了。
历史坐标里的老本们,视觉经验的享乐主义者,用沉甸甸的评价构筑了许多诸如“视觉文化”抽象莫测的概念,并且,引人遐思,竞人折腰。感觉上,视觉文化的规划似乎企图用种种未知的形象将空间填满,可这些形象不过是日常幻觉中剥离出的透明影像。空间在现实中是被划得支离破碎的,地缘的,种族的,宗教的,用经济学的官方语言说,于流动资本中被构建的。况且,分隔空间边界线的选择透过性又不会因为自身的透明性打折扣。
或许,我们压根不允许自己“看到”存于期许之外的东西。
所以别说,影像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。不然人家会说,思想有多远,你就给我滚多远!